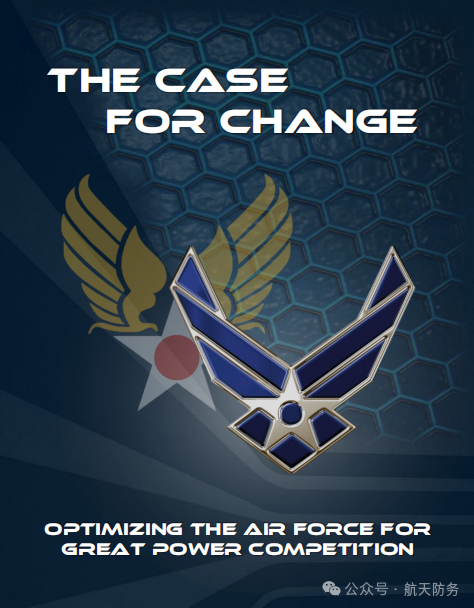
自1947年以来,美空军以人才培养、战备生成、力量投送、能力开发为核心,持续“拥抱适应性和变革”。
冷战期间(1947年-1991年)。美苏陷入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,核和常规武器竞赛不断升级。美空军优先发展隐形技术、精确技术,以弥补其在常规兵力中的数量劣势,寻求质量上的军事优势。
人才培养方面,培养以威慑为中心,具备“永远处于战争状态”的空军飞行员,可实现预先部署、标准化和快速、大规模动员。同时,这些飞行员可熟练执行特定任务。战备生成方面,强调基于现实威胁的高端训练、大规模动员演习,以及定期评估核战备力量的反应灵敏度。力量投送方面,广泛的海外基地网络和大量前沿设施,可实现美空军的快速动员。同时,美空军严重依赖用战略核力量威慑对手。能力开发方面,发展隐形飞机、精确制导武器、持久太空能力,以美国的技术优势抵消苏联在常规力量上的数量优势。
冷战结束后(1991-2001年)。海湾战争的胜利和苏联解体,推动了美军大规模裁军。美军利用灵活的空中力量在巴尔干半岛、前南斯拉夫共和国、伊拉克发动了一系列战争。
人才培养方面,在“和平红利”思想的影响下,美空军规模虽然大幅缩减,但在执行远征任务中具备了更成熟、熟练的技能。战备生成方面,战备状态侧重于区域性轮换,并开展间歇性的空中战役。美核库存缩减,核警戒状态下调,促进了常规力量的轮换。力量投送方面,整合海外基地,并在美中央司令部管辖范围内增加军事基础设施数量,以便大规模集结部队。能力开发方面,在缺乏同等对手的情况下,美空军能力开发越来越关注实现工业效率。
反恐战争期间(2001-2017年)。美空军通过持续轮换部署,支撑联合部队实现“按需的力量投送”和“按需的后勤保障”。同时,这一时期的技术和战术的创新多集中于满足“紧急需求”。
人才培养方面,具备高度适应性的美空军将被部署到“特殊的作战环境中”,执行非传统任务,并快速生成、获取超出训练范围的作战能力。战备生成方面,美空军通过优化供应链,进行作战需求管理,维持持续交战能力,以高效轮换和持续使用部队。力量投送方面,针对特定和多样化任务,发展灵活的作战能力,以夺取制空权。能力开发方面,紧急的作战需求加速驱动了采办流程向跨域灵活性和适应性发展。
重返大国竞争后(2017年-)。美空军认为,大国竞争时代呈现出4个特点。一是美军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等大国的威胁,增加了全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。二是低成本无人机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、高超声速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,标志着变革的到来。三是“国家行为者的侵略行为和不对称行动”挑战着传统作战方式。四是太空、网络领域的日益成熟和激烈竞争成为战争特征演变的关键。
人才培养方面,①培养“任务准备型”飞行员,以掌握适应各种作战场景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创造竞争优势。②简化飞行员的训练和教育计划,标准化飞行员的发展,促进飞行员对威胁环境形成“统一理解”,以期“在正确的地点、正确的时间、培养正确的空军人员”,并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干部储备。同时,培养一支具有凝聚力的部队。③强调超越教学大纲的技术培训,重点帮助飞行员了解威胁、任务指挥、防御的作用,实现在有争议的条件下预测和解决复杂、未定义的问题。④建立“技术准尉”晋升渠道,培养网络、计算机等关键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。
战备生成方面,①美空军战略由“功能准备”向“任务准备”转型,实施“以任务为中心”的评估和检查,并提高任务保障的有效性。②实施大规模演习和“以任务为中心”的训练,全面评估美空军快速集结和部署的能力,并增强部队凝聚力。③通过一个整体和基于风险的流程评估、审查、整合战备数据,为高级领导提供认知决策,确保美空军的战备评估与高端战争的需求保持一致。
力量投送方面,①创建连贯的、标准化的、定义明确的行动单元(可部署作战联队(Deployable Combat Wing)、就地作战联队(In-Place Combat Win)、战斗力生成联队(Combat Generation Wing)),以在作战第一天即具备作战效能。②行动单元具备3个层次(任务层、指挥层、维持层)。指挥层由高级领导和参谋人员组成,可执行整个行动单元的指挥和控制任务;任务层至少包括一个“任务生成兵力单元”,可根据任务进行多个“任务生成兵力单元”的任意重组;维持层包括标准化的作战支持,可向战区司令部“呈现清晰和可信的作战能力”,帮助美空军“看到自己”。③明确作战联队与基地指挥官之间的伙伴关系,使作战联队更专注于作战任务,基地指挥官更专注于在竞争、危机和冲突中维持基地运营。
能力开发方面,①建立单一、权威的“能力司令部”,优先考虑并协调美空军“一体化体系能力”与新技术的需求,以打破组织壁垒、开发关键作战能力。②推动跨平台任务系统集成和能力发展,实现“以平台为中心”的杀伤链向“集成的、以任务为中心”的“体系杀伤网络”转型。
个人观点。为赢得大国竞争,美空军以“没有时间了,必须坚持到底”的决心拉开变革的序幕。美空军的这场变革来势汹汹,但也困难重重,面临着资金、官僚制度、关键人物任期(比如肯德尔任期结束后,新任空军部部长能否继续推动变革仍然存疑)、保守派(如美国会要求对美空军的变革措施进行为期180天的审查),以及变革计划不成熟(美空军内部人员称,此次变革仍缺乏详细、具体的计划)等方面的困难。美空军也充分了解美海军陆战队“艰辛”的变革之路,但他们仍称,“拥抱变革不是选择,而是一种必然,美国空军将充满信心,继续前进”。
初审:孙世奇
复审:成自来
终审:陈光中
